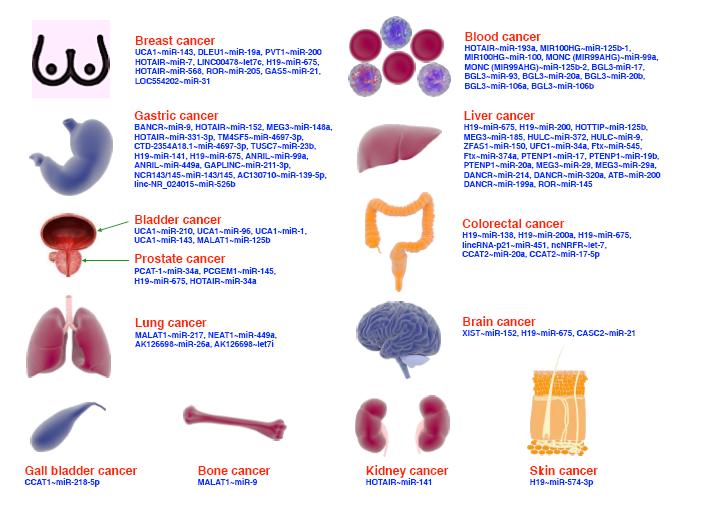引用本文: 张华, 张晓玲, 彭玲, 张鑫, 张兰兰. 表观遗传学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2, 21(2): 148-152. doi: 10.7507/1671-6205.202201040 复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是继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之后的第三次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及安全,已成为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卫生威胁之一[1]。表观遗传调控是指在DNA序列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表达、功能和表型发生可遗传的变化,包括DNA甲基化、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ncRNA)和组蛋白修饰等,主要通过对基因转录或翻译过程进行调控,影响其功能和特性[2]。表观遗传修饰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如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在新冠肺炎中许多表观遗传通路也发生了变化[3]。本文将对在新冠肺炎中主要表观遗传调控方式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做详细介绍。
1 新冠肺炎发病机制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的直接入侵是新冠肺炎致病的主要原因[4]。SARS-CoV-2与SARS‑CoV和MERS‑CoV类似,也依赖于表面的刺突糖蛋白(spike glycoprotein,S蛋白)识别结合宿主细胞。S蛋白包含两个亚基—S1和S2。S1含有受体结合结构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BRD),促进识别膜受体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ngiotensin I converting enzyme 2,ACE2);S2能够促进膜融合增强病毒侵入能力[5]。ACE2已被确定为SARS-CoV-2的功能宿主受体。SARS-CoV-2病毒通过S蛋白与ACE2受体结合进入宿主靶细胞,启动感染程序[6]。研究发现S蛋白的BRD是高度可变的,与SARS-CoV相比,SARS-CoV-2中影响BRD结合的6个氨基酸中有5个发生了变化,这可能导致SARS-CoV-2与ACE2受体亲和力更强,感染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6-8]。除了ACE2外,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2,TMPRSS2)也是SARS-CoV-2感染的关键调节因子。TMPRSS2激活可激活附着在ACE2上的S蛋白,导致SARS-CoV-2内吞或直接膜融合进入宿主细胞,这是SARS-CoV-2进入宿主细胞的关键因素[3, 9-11]。复杂而有序地调控网络维持着机体免疫[12-14],而当细菌、病毒、创伤等外部刺激后,短时间内造成过激的炎症,炎症失控致细胞因子风暴是新冠肺炎病理损伤的关键机制[15]。新冠肺炎患者免疫功能失调引起细胞因子风暴,导致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IL-6、IL-17、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人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肿瘤坏死因子-α等水平升高,引起广泛的肺部炎症,加重病情,甚至引起感染性休克、多器官衰竭等并发症[16-18]。新冠肺炎患者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可能进一步激活促炎信号通路,如JAK-STAT通路,加重病情[19]。新冠肺炎患者自然杀伤细胞明显升高,恢复期的新冠肺炎患者CD8+ T淋巴细胞高表达,CD4+ T淋巴细胞抑制分子上调和活化分子下调以及Tfh样细胞低表达,这有助于体内免疫应答平衡。炎症与细胞因子风暴是新冠肺炎的重要特征,因此它们在新冠肺炎中发生重要作用[12-14]。
2 新冠肺炎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2.1 DNA甲基化与新冠肺炎
DNA甲基化是哺乳动物最主要的表观遗传调控方式,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要调节因子,在新冠肺炎基因表达调控中起重要作用。DNA甲基化通路可以调控SARS-CoV-2宿主膜受体ACE2的表达,促进SARS-CoV-2感染[20]。SARS-CoV-2可引起DNA甲基化水平改变,影响免疫应答抑制因子的表达水平,加剧新冠肺炎进程[21]。SARS-CoV-2感染可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DNA甲基化失调,导致ACE2基因低甲基化,引起ACE2异常高表达,而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的干扰素调节基因、核因子-κB等免疫应答过程关键调节因子的去甲基化导致其表达升高,可能加剧SARS-CoV-2引起的免疫反应,增加细胞因子风暴及对SARS-CoV-2的易感性[22-24]。肺腺癌、胃腺癌、结肠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患者的肿瘤组织中ACE2发生DNA低甲基化,导致ACE2异常的高表达,增加癌症患者感染SARS-CoV-2风险[25-26]。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基因座的4个CpG位点和启动子区的一个CpG位点发生低甲基化,导致其更易感染SARS-CoV-2[27-28]。研究表明,SARS-CoV-2感染引起的病毒特异性甲基化区域中约70%发生低甲基化,上皮细胞亲和性的病毒(如腺病毒、肠道病毒D68、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和SARS-CoV-2)都有明显的转录调控区去甲基化现象[29]。新冠肺炎患者血液中75%与急性疾病相关的差异甲基化区域位于基因启动子内,并发生低甲基化,因此新冠肺炎患者发生的DNA低甲基化可能引发SARS-CoV-2病毒受体基因的高表达。
DNA甲基化与新冠肺炎的临床严重程度密切相关[30-31]。Rathod等[32]研究发现DNA甲基化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这解释了成人新冠肺炎患者的易感性、发病率和病死率高于儿童患者;同时发现男性与女性比,ACE2基因的DNA甲基化水平更高,而CD40LG基因的DNA甲基化水平较低。羟基氯喹可以治疗多种炎症性疾病,并用于新冠肺炎的治疗,细胞色素P450是羟氯喹代谢的关键调节因子,DNA甲基化可以影响细胞色素P450的表达水平,从而可能影响羟基氯喹代谢,增加新冠肺炎患者视网膜病变风险[33]。环境毒物全氟辛酸暴露引起小鼠DNA甲基转移酶表达水平降低,增加ACE2和TMPRSS2的表达水平,增强小鼠对SARS-CoV-2的易感性[34]。
2.2 ncRNA与新冠肺炎
ncRNA主要包括微RNA(microRNA,miRNA)和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ncRNA表达异常可以引发多种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及炎症等,并且ncRNA可以参与调控新冠肺炎[35]。SARS-CoV-2基因与人ncRNA序列具有Watson-Crick核苷酸互补性,其异常结合可能会破坏靶基因ncRNA的表观遗传调控[36]。
宿主miRNA与SARS-CoV-2病毒的相互作用可以调控宿主免疫信号通路来促进新冠肺炎发病进程[37]。SARS-CoV-2病毒基因组中的miRNA可以通过激活纤维化相关的通路和调节先天免疫系统来诱导SARS-CoV-2感染[38]。miR-18a和miR-125b可以调节ACE2的表达,其中,miR-18在调节新冠肺炎相关肾病的ACE2表达中起关键作用[39]。miRNA(miR-124-3p)、lncRNA(Gm26917)、circRNAs(Ppp1r10、C330019G07Rik)和mRNA(Ddx58)可以组成相互竞争的内源性RNA(competing endogenous RNAs,ceRNA),可以调节靶向特定mRNA的miRNAs的表达,病毒可以通过ceRNA效应利用宿主miRNA网络。因此,ceRNA在研究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及抗病毒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研究SARS-CoV-2的发病进程[40]。SARS-CoV-2表达一种类似miRNA的小RNA CoV2-miR-O7a,能够利用RNA干扰选择性地抑制宿主基因表达[41]。miRNA对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1(poly adenosine diphosphate ribose polymerase 1,PARP-1]的调节在细胞存活、氧化还原平衡、DNA损伤反应、能量稳态和其他细胞过程起重要作用,miRNA/PARP-1轴有利于SARS-CoV-2宿主的靶向调节[42]。SARS-CoV-2 RNA基因组中miRNA结合位点有助于RNA相关药物的研发[43]。中到重度新冠肺炎患者的miR-146a-5p、miR-21-5p和miR-142-3p持续下调,而miR-15b-5p持续上调,因此miR-146a-5p、miR-21-5p、miR-142-3p和miR-15b-5p可以作为新冠肺炎进展的生物标志物[44]。miRNA可以调控新冠肺炎患者免疫反应,干扰基因表达,可以用于新冠肺炎药物研发及诊疗。
lncRNA也参与调控新冠肺炎进程。SARS-CoV-2感染的肺上皮细胞RNA测序,发现了21个差异表达的lncRNA,这些lncRNA广泛参与病毒增殖、细胞存活、信号通路和免疫反应[45-46]。IL-6和NLRP3炎性小体是病原体感染后免疫反应刺激的主要免疫成分,lncRNA可调节IL-6的分泌和NLRP3炎性小体的形成,进而调控细胞因子风暴[47]。干扰素调节因子(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IRF)1、IRF4、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蛋白(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1和STAT3可调节lncRNA的表达以影响SARS-CoV-2感染,失调的lncRNA参与许多病毒感染、炎症和免疫功能相关的通路,表明lncRNA可能参与抗病毒反应[48]。SARS-CoV-2感染引起多种lncRNA(WAKMAR2、EGOT、EPB41L4A-AS1、ENSG00000271646、AC131011.2、AC007298.2、NEAT1、MALAT1等)的表达显著升高,进而参与SARS-CoV-2 感染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和抗病毒反应[49-51]。因此,lncRNA可能与SARS-CoV-2感染引起的炎症发展有关[52],并有可能作为新冠肺炎的生物标志物。SARS-CoV-2可能通过ACE2和TMPRSS2引起睾丸生殖障碍,睾丸组织特异性表达的lncRNA(如GRM7-AS3)可能是研究新冠肺炎与男性不育可能相关的潜在生物标志物[53]。新冠肺炎患者维生素D受体与SNHG6、SNHG16、Linc00511、Linc00346等多种lncRNA的表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维生素D受体、SNHG6和SNHG16等可能是新冠肺炎感染的原因[54]。因此,lncRNA可以调节新冠肺炎相关的炎症反应并用于新冠肺炎的诊疗。
2.3 组蛋白修饰与新冠肺炎
组蛋白修饰包括组蛋白的乙酰化、磷酸化、甲基化、磺酰化和泛素化等,可以改变染色质状态和基因表达,在许多细胞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55]。组蛋白修饰可以调节ACE2的表达。新冠肺炎患者肺组织中ACE2表达升高,相关性分析显示组蛋白修饰相关基因HAT1、HDAC2和KDM5B是ACE2的潜在调节因子[56]。组蛋白甲基转移酶EZH2可以催化ACE2启动子区域的H3K27me3,SARS‑CoV-2感染后哺乳动物细胞ACE2的表达明显增强,H3K27me3的水平明显降低,EZH2可以介导H3K27me3抑制哺乳动物细胞ACE2的表达[57]。SARS‑CoV-2感染后激活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引起重度新冠肺炎的标志性炎症因子γ-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α和干扰素刺激基因明显上调,导致组蛋白修饰异常,引起H3K4me3水平降低,进一步诱导细胞因子风暴[3, 58-59]。组蛋白H3瓜氨酸化(citrullination of histone H3,Cit-H3)也参与调控新冠肺炎,新冠肺炎患者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的标志物Cit-H3水平明显升高[60]。组蛋白脱乙酰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是组蛋白乙酰化的重要调控因子,HDAC抑制剂可以增加组蛋白的乙酰化程度,临床HDAC抑制剂罗米地辛、帕比司他、西丁醇、CAY10603等能够抑制内吞作用并削弱ACE2识别来抑制SARS-CoV-2进入宿主细胞[61]。HDAC可以结合到ACE2启动子并促进ACE2的表达,HDAC抑制剂可以阻止SARS-CoV-2与宿主结合,ACE/ACE2–血管紧张素Ⅱ的1型受体–胆固醇–HDAC轴参与调控新冠肺炎,即SARS-CoV-2病毒S蛋白与ACE2的结合(由胆固醇促进)导致血管紧张素Ⅱ的1型受体激活,增加HDAC活性并上调ACE2的表达,而HDAC激活,导致组蛋白去乙酰化,可促进胆固醇合成[62]。HDAC抑制剂丙戊酸可以降低ACE2和TMPRSS2的表达,调节免疫应答,具有抗血栓、抗血小板和抗炎作用,能够减少新冠肺炎终末器官的损伤[63]。因此,组蛋白修饰可以调节ACE2水平,调控SARS-CoV-2感染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及新冠肺炎终末器官损伤。
3 总结与展望
新冠肺炎是目前最受关注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SARS-CoV-2感染过程中会发生表观遗传变化,其表观遗传机制尚不明确,并且表观遗传在SARS‑CoV-2侵入、免疫应答及炎症风暴等新冠肺炎致病机制方面的研究较浅,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以促进表观遗传相关药物的开发。
表观遗传修饰既调节抗病毒基因的表达,也调节用于病毒有效复制和传播的宿主因子的表达[3]。表观遗传修饰参与新冠肺炎中ACE2和TMPRSS2的异常表达、细胞因子风暴及免疫应激。ACE2和TMPRSS2的表观遗传调节对于SARS-CoV-2感染至关重要,针对SARS-CoV-2的细胞进入过程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治疗策略。由于ACE2和TMPRSS2在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ACE2和TMPRSS2的表观遗传机制治疗可能有助于治疗SARS-COV-2感染,某些ACE2和TMPRSS2的抑制剂(包括表观遗传相关抑制剂)正在进行临床试验。ACE2受体广泛分布于人多种细胞类型,如血管内皮细胞、肺泡上皮细胞、平滑肌细胞等,对新冠肺炎的治疗带来了额外的挑战[64]。尽管表观遗传调控新冠肺炎的致病机制有待于更充分的探索,但表观遗传修饰异常显然是新冠肺炎致病的重要原因,表观遗传相关调控因子(ncRNA、HDAC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治疗靶点或生物学标志物。
利益冲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是继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之后的第三次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及安全,已成为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卫生威胁之一[1]。表观遗传调控是指在DNA序列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表达、功能和表型发生可遗传的变化,包括DNA甲基化、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ncRNA)和组蛋白修饰等,主要通过对基因转录或翻译过程进行调控,影响其功能和特性[2]。表观遗传修饰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如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在新冠肺炎中许多表观遗传通路也发生了变化[3]。本文将对在新冠肺炎中主要表观遗传调控方式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做详细介绍。
1 新冠肺炎发病机制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的直接入侵是新冠肺炎致病的主要原因[4]。SARS-CoV-2与SARS‑CoV和MERS‑CoV类似,也依赖于表面的刺突糖蛋白(spike glycoprotein,S蛋白)识别结合宿主细胞。S蛋白包含两个亚基—S1和S2。S1含有受体结合结构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BRD),促进识别膜受体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ngiotensin I converting enzyme 2,ACE2);S2能够促进膜融合增强病毒侵入能力[5]。ACE2已被确定为SARS-CoV-2的功能宿主受体。SARS-CoV-2病毒通过S蛋白与ACE2受体结合进入宿主靶细胞,启动感染程序[6]。研究发现S蛋白的BRD是高度可变的,与SARS-CoV相比,SARS-CoV-2中影响BRD结合的6个氨基酸中有5个发生了变化,这可能导致SARS-CoV-2与ACE2受体亲和力更强,感染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6-8]。除了ACE2外,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2,TMPRSS2)也是SARS-CoV-2感染的关键调节因子。TMPRSS2激活可激活附着在ACE2上的S蛋白,导致SARS-CoV-2内吞或直接膜融合进入宿主细胞,这是SARS-CoV-2进入宿主细胞的关键因素[3, 9-11]。复杂而有序地调控网络维持着机体免疫[12-14],而当细菌、病毒、创伤等外部刺激后,短时间内造成过激的炎症,炎症失控致细胞因子风暴是新冠肺炎病理损伤的关键机制[15]。新冠肺炎患者免疫功能失调引起细胞因子风暴,导致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IL-6、IL-17、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人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肿瘤坏死因子-α等水平升高,引起广泛的肺部炎症,加重病情,甚至引起感染性休克、多器官衰竭等并发症[16-18]。新冠肺炎患者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可能进一步激活促炎信号通路,如JAK-STAT通路,加重病情[19]。新冠肺炎患者自然杀伤细胞明显升高,恢复期的新冠肺炎患者CD8+ T淋巴细胞高表达,CD4+ T淋巴细胞抑制分子上调和活化分子下调以及Tfh样细胞低表达,这有助于体内免疫应答平衡。炎症与细胞因子风暴是新冠肺炎的重要特征,因此它们在新冠肺炎中发生重要作用[12-14]。
2 新冠肺炎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2.1 DNA甲基化与新冠肺炎
DNA甲基化是哺乳动物最主要的表观遗传调控方式,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要调节因子,在新冠肺炎基因表达调控中起重要作用。DNA甲基化通路可以调控SARS-CoV-2宿主膜受体ACE2的表达,促进SARS-CoV-2感染[20]。SARS-CoV-2可引起DNA甲基化水平改变,影响免疫应答抑制因子的表达水平,加剧新冠肺炎进程[21]。SARS-CoV-2感染可引起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DNA甲基化失调,导致ACE2基因低甲基化,引起ACE2异常高表达,而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的干扰素调节基因、核因子-κB等免疫应答过程关键调节因子的去甲基化导致其表达升高,可能加剧SARS-CoV-2引起的免疫反应,增加细胞因子风暴及对SARS-CoV-2的易感性[22-24]。肺腺癌、胃腺癌、结肠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患者的肿瘤组织中ACE2发生DNA低甲基化,导致ACE2异常的高表达,增加癌症患者感染SARS-CoV-2风险[25-26]。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基因座的4个CpG位点和启动子区的一个CpG位点发生低甲基化,导致其更易感染SARS-CoV-2[27-28]。研究表明,SARS-CoV-2感染引起的病毒特异性甲基化区域中约70%发生低甲基化,上皮细胞亲和性的病毒(如腺病毒、肠道病毒D68、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和SARS-CoV-2)都有明显的转录调控区去甲基化现象[29]。新冠肺炎患者血液中75%与急性疾病相关的差异甲基化区域位于基因启动子内,并发生低甲基化,因此新冠肺炎患者发生的DNA低甲基化可能引发SARS-CoV-2病毒受体基因的高表达。
DNA甲基化与新冠肺炎的临床严重程度密切相关[30-31]。Rathod等[32]研究发现DNA甲基化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这解释了成人新冠肺炎患者的易感性、发病率和病死率高于儿童患者;同时发现男性与女性比,ACE2基因的DNA甲基化水平更高,而CD40LG基因的DNA甲基化水平较低。羟基氯喹可以治疗多种炎症性疾病,并用于新冠肺炎的治疗,细胞色素P450是羟氯喹代谢的关键调节因子,DNA甲基化可以影响细胞色素P450的表达水平,从而可能影响羟基氯喹代谢,增加新冠肺炎患者视网膜病变风险[33]。环境毒物全氟辛酸暴露引起小鼠DNA甲基转移酶表达水平降低,增加ACE2和TMPRSS2的表达水平,增强小鼠对SARS-CoV-2的易感性[34]。
2.2 ncRNA与新冠肺炎
ncRNA主要包括微RNA(microRNA,miRNA)和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ncRNA表达异常可以引发多种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及炎症等,并且ncRNA可以参与调控新冠肺炎[35]。SARS-CoV-2基因与人ncRNA序列具有Watson-Crick核苷酸互补性,其异常结合可能会破坏靶基因ncRNA的表观遗传调控[36]。
宿主miRNA与SARS-CoV-2病毒的相互作用可以调控宿主免疫信号通路来促进新冠肺炎发病进程[37]。SARS-CoV-2病毒基因组中的miRNA可以通过激活纤维化相关的通路和调节先天免疫系统来诱导SARS-CoV-2感染[38]。miR-18a和miR-125b可以调节ACE2的表达,其中,miR-18在调节新冠肺炎相关肾病的ACE2表达中起关键作用[39]。miRNA(miR-124-3p)、lncRNA(Gm26917)、circRNAs(Ppp1r10、C330019G07Rik)和mRNA(Ddx58)可以组成相互竞争的内源性RNA(competing endogenous RNAs,ceRNA),可以调节靶向特定mRNA的miRNAs的表达,病毒可以通过ceRNA效应利用宿主miRNA网络。因此,ceRNA在研究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及抗病毒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研究SARS-CoV-2的发病进程[40]。SARS-CoV-2表达一种类似miRNA的小RNA CoV2-miR-O7a,能够利用RNA干扰选择性地抑制宿主基因表达[41]。miRNA对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1(poly adenosine diphosphate ribose polymerase 1,PARP-1]的调节在细胞存活、氧化还原平衡、DNA损伤反应、能量稳态和其他细胞过程起重要作用,miRNA/PARP-1轴有利于SARS-CoV-2宿主的靶向调节[42]。SARS-CoV-2 RNA基因组中miRNA结合位点有助于RNA相关药物的研发[43]。中到重度新冠肺炎患者的miR-146a-5p、miR-21-5p和miR-142-3p持续下调,而miR-15b-5p持续上调,因此miR-146a-5p、miR-21-5p、miR-142-3p和miR-15b-5p可以作为新冠肺炎进展的生物标志物[44]。miRNA可以调控新冠肺炎患者免疫反应,干扰基因表达,可以用于新冠肺炎药物研发及诊疗。
lncRNA也参与调控新冠肺炎进程。SARS-CoV-2感染的肺上皮细胞RNA测序,发现了21个差异表达的lncRNA,这些lncRNA广泛参与病毒增殖、细胞存活、信号通路和免疫反应[45-46]。IL-6和NLRP3炎性小体是病原体感染后免疫反应刺激的主要免疫成分,lncRNA可调节IL-6的分泌和NLRP3炎性小体的形成,进而调控细胞因子风暴[47]。干扰素调节因子(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IRF)1、IRF4、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蛋白(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1和STAT3可调节lncRNA的表达以影响SARS-CoV-2感染,失调的lncRNA参与许多病毒感染、炎症和免疫功能相关的通路,表明lncRNA可能参与抗病毒反应[48]。SARS-CoV-2感染引起多种lncRNA(WAKMAR2、EGOT、EPB41L4A-AS1、ENSG00000271646、AC131011.2、AC007298.2、NEAT1、MALAT1等)的表达显著升高,进而参与SARS-CoV-2 感染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和抗病毒反应[49-51]。因此,lncRNA可能与SARS-CoV-2感染引起的炎症发展有关[52],并有可能作为新冠肺炎的生物标志物。SARS-CoV-2可能通过ACE2和TMPRSS2引起睾丸生殖障碍,睾丸组织特异性表达的lncRNA(如GRM7-AS3)可能是研究新冠肺炎与男性不育可能相关的潜在生物标志物[53]。新冠肺炎患者维生素D受体与SNHG6、SNHG16、Linc00511、Linc00346等多种lncRNA的表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维生素D受体、SNHG6和SNHG16等可能是新冠肺炎感染的原因[54]。因此,lncRNA可以调节新冠肺炎相关的炎症反应并用于新冠肺炎的诊疗。
2.3 组蛋白修饰与新冠肺炎
组蛋白修饰包括组蛋白的乙酰化、磷酸化、甲基化、磺酰化和泛素化等,可以改变染色质状态和基因表达,在许多细胞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55]。组蛋白修饰可以调节ACE2的表达。新冠肺炎患者肺组织中ACE2表达升高,相关性分析显示组蛋白修饰相关基因HAT1、HDAC2和KDM5B是ACE2的潜在调节因子[56]。组蛋白甲基转移酶EZH2可以催化ACE2启动子区域的H3K27me3,SARS‑CoV-2感染后哺乳动物细胞ACE2的表达明显增强,H3K27me3的水平明显降低,EZH2可以介导H3K27me3抑制哺乳动物细胞ACE2的表达[57]。SARS‑CoV-2感染后激活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引起重度新冠肺炎的标志性炎症因子γ-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α和干扰素刺激基因明显上调,导致组蛋白修饰异常,引起H3K4me3水平降低,进一步诱导细胞因子风暴[3, 58-59]。组蛋白H3瓜氨酸化(citrullination of histone H3,Cit-H3)也参与调控新冠肺炎,新冠肺炎患者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的标志物Cit-H3水平明显升高[60]。组蛋白脱乙酰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是组蛋白乙酰化的重要调控因子,HDAC抑制剂可以增加组蛋白的乙酰化程度,临床HDAC抑制剂罗米地辛、帕比司他、西丁醇、CAY10603等能够抑制内吞作用并削弱ACE2识别来抑制SARS-CoV-2进入宿主细胞[61]。HDAC可以结合到ACE2启动子并促进ACE2的表达,HDAC抑制剂可以阻止SARS-CoV-2与宿主结合,ACE/ACE2–血管紧张素Ⅱ的1型受体–胆固醇–HDAC轴参与调控新冠肺炎,即SARS-CoV-2病毒S蛋白与ACE2的结合(由胆固醇促进)导致血管紧张素Ⅱ的1型受体激活,增加HDAC活性并上调ACE2的表达,而HDAC激活,导致组蛋白去乙酰化,可促进胆固醇合成[62]。HDAC抑制剂丙戊酸可以降低ACE2和TMPRSS2的表达,调节免疫应答,具有抗血栓、抗血小板和抗炎作用,能够减少新冠肺炎终末器官的损伤[63]。因此,组蛋白修饰可以调节ACE2水平,调控SARS-CoV-2感染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及新冠肺炎终末器官损伤。
3 总结与展望
新冠肺炎是目前最受关注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SARS-CoV-2感染过程中会发生表观遗传变化,其表观遗传机制尚不明确,并且表观遗传在SARS‑CoV-2侵入、免疫应答及炎症风暴等新冠肺炎致病机制方面的研究较浅,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以促进表观遗传相关药物的开发。
表观遗传修饰既调节抗病毒基因的表达,也调节用于病毒有效复制和传播的宿主因子的表达[3]。表观遗传修饰参与新冠肺炎中ACE2和TMPRSS2的异常表达、细胞因子风暴及免疫应激。ACE2和TMPRSS2的表观遗传调节对于SARS-CoV-2感染至关重要,针对SARS-CoV-2的细胞进入过程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治疗策略。由于ACE2和TMPRSS2在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ACE2和TMPRSS2的表观遗传机制治疗可能有助于治疗SARS-COV-2感染,某些ACE2和TMPRSS2的抑制剂(包括表观遗传相关抑制剂)正在进行临床试验。ACE2受体广泛分布于人多种细胞类型,如血管内皮细胞、肺泡上皮细胞、平滑肌细胞等,对新冠肺炎的治疗带来了额外的挑战[64]。尽管表观遗传调控新冠肺炎的致病机制有待于更充分的探索,但表观遗传修饰异常显然是新冠肺炎致病的重要原因,表观遗传相关调控因子(ncRNA、HDAC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治疗靶点或生物学标志物。
利益冲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